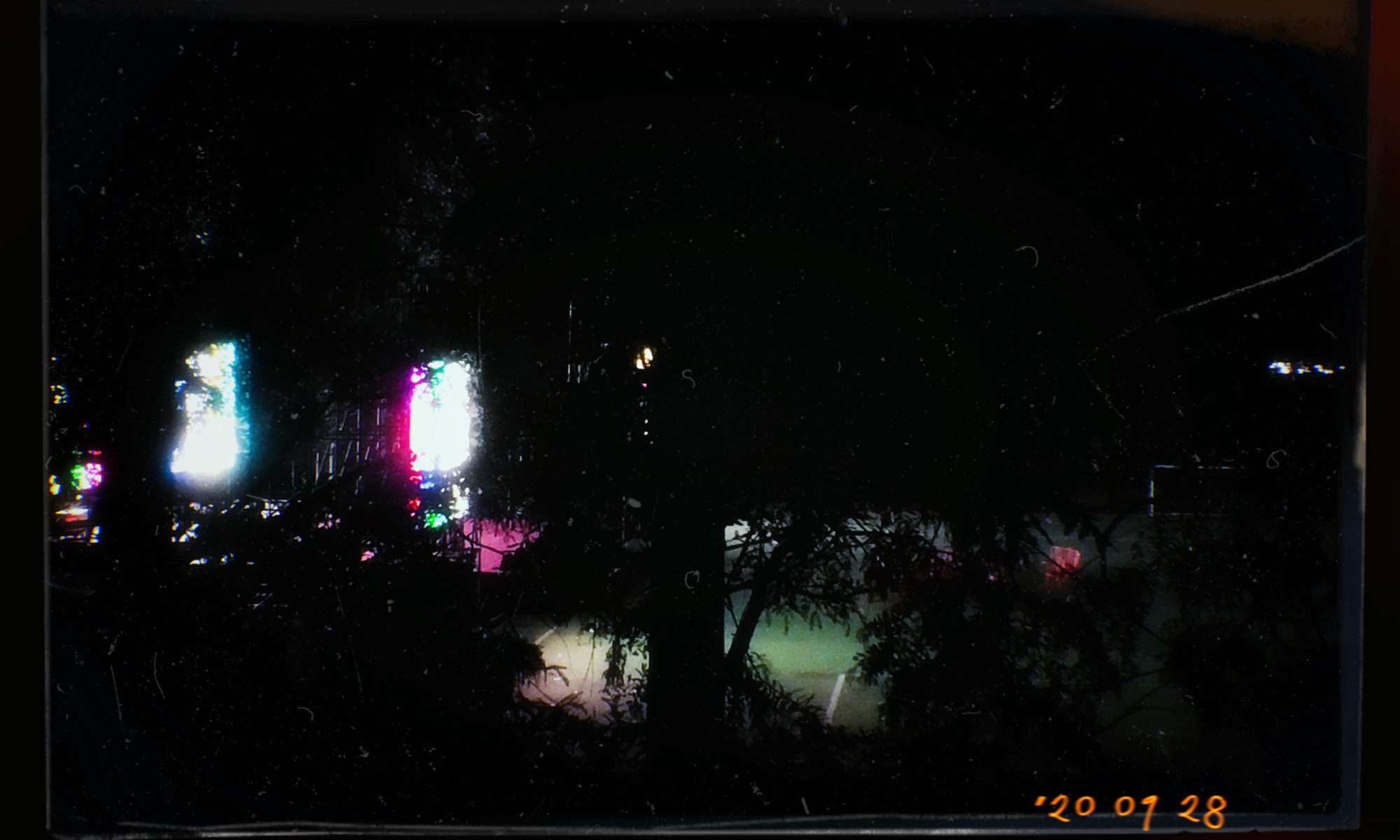这是1776 1064 7703给我的,最后的,永远的遗物
Y: “果然没有希望了。”
BG:“一直如此,希望不过感性之物,理论上来讲只有‘0’与‘1’。”
“于是希望便是介于‘0’与‘1’之间的存在。”
“拗不过你。
”有人说除了最基本的温饱之外,人还需要希望赖以生存,可为什么我在失掉希望后还能苟活着呢?“
”要么你不能算是‘人’,要么就是你现在的状态不能成为活着。”
“你好过分欸……可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只能接受这样的批判。”
“谁又知道些什么呢?谁不是生存在混沌中挣扎着,抓住虚无,然后内心假定那就是救命稻草,在自我欺骗与迷幻中走向灭亡。”
“生活在梦里,就像……果然只有在梦里才能拥有……一种不能称为愉快的欣喜之情……是的,梦幻,扭曲了一切法则与认知的为所欲为的国度,在那里,一切都像是披上了雪银色的月光……”
”不可能一直处于梦中,醒醒,你需要生活。“
”那就让我一直生活在梦里,永远不醒来!“
”可悲,受困于自制的茧中,却没有破茧而出的动力与勇气。“
“……”
“……”
“好冷。“
”就算是正午也觉得冷吗?“
”嗯。“
”下去吃点什么吧。“
”你稍微扶一下我……“
”还以为你腿的旧伤好了呢,小心点。“
”我一直在想,这里似乎一成不变总是这样单调的白墙,多年以来一直如此,反倒是本应视为污垢的脚印成了装饰,真是……“
”有点儿讽刺?“
”有点令人欣慰与安心……就是我希望印子的颜色不要这么单调罢了。“
”颜色多了,不会觉得混杂吗?“
”不会啊,只有太单调才会觉得不合适。这样一类东西,不论被染上了多少种不同的颜色都不会有关系,正是颜色的混杂才能凸显出它的美好,才能成就它。如果可以,真希望能自由地给它上色……呀!这里有个转角,小心!“
”抱歉!刚刚在脑中构画色彩斑斓的墙……的确不错啊。只是他们大概永远不会同意吧。“
”’大概‘,也就是说还是有希望的。“
”……“
”这里我能自己走了,谢谢。“
”……“
Y:”c套餐,谢谢。“
BG:”a套餐,谢谢。“
”阳光房?“
”阳光房。“
”你还是不肯吃肉啊。”
“有问题?”
“到底是为什么?宗教?信仰?“
”你知道的,我是无神论者,我也不会对那些猪牛羊心存怜悯。“
”所以?“
”单纯是因为肉过于油腻,相比于蔬菜的清爽令我感到不适。”
“你说了算。”
“说到宗教,你现在还是一名自由宗教主义者,对吧?”
“你又要来‘传教’?”
“你怎么把筷子放下来了?……也罢,我的‘传教’你爱听不听。但我对这件事的看法而非这客观的‘教义’,请你再听几句吧。”
“……”
“宗教毕竟是为了团结人心而来,在远古时期,为了消除对未知的恐惧,人们拥有自己的图腾,为每一次‘神灵带给他们的胜利’而欣喜,于是士气被鼓舞,人心团结起来,氏族得以扩大,繁荣,一步步战胜恐惧。诚然,人类的发展中,宗教功不可没。可是后来呢?宗教成了分裂人心的工具,人们只因脑子里拥有不同的所谓‘信仰’也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坚信着的幻象与谎言而自相残杀,忘恩负义,中世纪如此,现在亦是如此。说到底,神与宗教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具象化的幻觉与谎言罢了,如今这样谎言能带给我们的好处已尽,坏处显现,放弃他们才是文明与理性的体现。”
“你说的事实一点儿不错,但你忽视了很多点。”
“料到你会这么说。”
“宗教也许真的是为了团结人心而来,但它的目标不止于此。对于我,我能在宗教中得到一丝救赎。”
“救赎?……有趣。‘
”宗教给了我……意义,也就是说……”
“打住,你是说你活下来的意义是宗教给予的?在信仰宗教前生活没有意义?”
“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你信仰宗教的原因只能是你太过于懦弱了,连自己活下来的意义都丧失了,不信任自己,转而去相信谎言,还是要劝劝你……”
“我的确不能确定信仰的真实与否,但至少让懦弱的我有个依靠吧,这又有什么错呢?”
BG:“…….”
Y:“反问你一句,没有宗教,你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努力地感受世间万物。”
“就算是不美好的……”
“也要去体验,去感受。”
“诶?”
“我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充实我的世界。”
“具体一点。”
“一成不变的生活让我的感官麻木,不再清醒,只有不断变换着的外界事物才能让我感受到些什么,让我得知……我还活着。”
“也就是说,你认为或者是因为清醒的精神状态?”
“以及能够维持清醒的自由。”
“嘛,至少我们在热爱生命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大起大落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啊,想想看:极端的沉沦,极端的欢乐,极端的扭曲,极端的苦素与平淡。我正是为了这些感觉而活,生命也不过是由这些感觉堆砌起来的,而我热爱生命。”
“作为一名唯心主义者,说出这些话也倒挺符合你的身份。”
“我吃完了。”
“不用等我,你先上去好了。”
“……”
Y:“《退步主义者》,让我猜猜,作者是太宰……”
“不,是坂口安吾。”
“我一直以为你是太宰治铁粉。”
“那么你一直以来都错了,同是无赖派,那家伙却主要是酒鬼,懦夫。”
“安吾也差不了多少哦。”
“我并没有否定身为MC(与故事本身无关的编者注:即”我的喜剧演员“,出自太宰治《斜阳》)时的太宰,但太宰治只有身为MC时才是真正的太宰,一个温柔到不行的人,其余时间一直处于宿醉的狂乱状态,看看他临终前写的东西吧。”
“《goodbye》也还好,其他的‘晚年’作品……考虑到那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心中’(编者注:即殉情)……确实。但坂口也说过他之所以癫狂是因为自己的作品过于健全……”
“就像我。”
“哪里?你不算癫狂啦……只是性格过于多变,罢了。”
“哼。”
“你的作品倒是真的很不错。”
“哼。”
“你还是不喜欢别人这样夸你啊。”
“不喜欢太直白的夸奖,毕竟这样的夸奖多半是虚伪的,我scribble的东西没那么好。”
“我是认真的。”
“……谢谢。”
BG:“今天留校?”
Y:”有点不想那么早回去,和家里人说过了。“
”……了解。“
”最后一个圣诞,也过去了呢。“
”会不会,不是’最后‘呢?“
”我不知道。“
”……也对,什么都没办法知道。“
”虽然你我都祈求这并非最后,但我面对这个问题的确只能理性回答’我不知道。‘世上本无完全确定之物,所有的事物都在相互否定着——就连过去的事也不能成为定数,因此,世界上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应是’我不知道‘”
“除了现在,此时此刻。”
“这也是为什么此刻永远是最美妙的。”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气温,合适的日期,合适的风,合适的……人。“
”还可以为之感到幸运的是,对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由谁来打破这一切?‘这个问题的答案,回答仍然是’我不知道‘“
”……“
”’我不知道‘,令人安心十分,仿佛鼹鼠钻入自己温暖地洞般的四个字。“
”很符合你的作风……吧。“
BG:“说到作风,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Y:“我给人的感觉的确如此吧,不是很会贸然加入别的群体的别的话题,却总是会在自己那个小群体里畅所欲言,滔滔不绝。”
“领教过了,你口中那种贸然加入别的群体的别的话题那种人指的是我吧。”
“嘿嘿,可能哦。”
“说实话我认为我这一点特性很招人厌,什么方面好像都懂一点,但是深挖下去就没什么内涵,充其量只不过是在同样不是很了解的人面前侃大哈罢了。所谓Mr.know’it’all。”
“同样是什么都懂一点,貌似有点过了就不是博学或者versatile了,而是贬义的万事通know‘it’all,我懂。但我认为这也是你的社交圈广泛的缘故,你似乎和什么人都聊得来,不像我……”
“毕竟,你只会对自己认可的人敞开心扉啊。”
“你不也是……”
“只会想要见到想见的人,对于不想见的人一点联系也不希望产生,大概就是这样。却也总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
“怎么去界定‘保护自己’?”
“如果避开见到的人会勾起自己一些不美好的回忆,如果避免交往的人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如果不希望产生联系的人会在一产生联系后对你造成困扰,那么,避开了就是在保护自己。”
“真是一种懦弱的行为啊……”
“不,是聪明.”
“为什么?”
“我做不到不去见不想见的人,或者说一部分的我竭力告诉自己如果去见了那个人后会造成的无可逆转的伤害,而剩下的我却强硬地主导我去见那个人。明明知道了积攒而来赖以生存的希望会在那一刻崩坏,明明知道这样下去会继续困扰到那个人,却还是愚钝地想要去见到那个人。也许我就是这样自私自利。”
“如果有这样的人烦我的话,我的确会火冒三丈,觉得厌烦……但,兴许我还会关注着那个人,关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确认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存在。”
“这样说,我姑且还是继续愚钝下去好了……”
“9.8……关于死,你是怎么看的。”
“怎么突然提这种话题?”
“想到了就说嘛。”
“……那又怎么界定‘生’呢?”
“让我听听你的解释。”
“我先前提到了人的世界是由知觉形成的,不,姑且说人的世界就是人的知觉全部:五官对应的五种知觉,再加上思想和记忆。但是感官,知觉,意识这类东西毕竟和人体的最高中枢‘脑’的联系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于是人们界定了一种连接感官意识与物质的大脑的东西——感受质‘qualia’,人们就是因为有感受质才能感受到一切,也就是所谓活着。如果没有这种东西,那么我们拥有再多的感官,再健全聪明的大脑也无济于事。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失掉了qualia,那么当真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了的人,就能界定为死亡。”
“好冷峻哦。你不会相信任何形式的死后世界吧。”
“死后?那不是人们的感知范围。”
“如果硬要你想象死亡的话……”
“就当是睡大觉。”
“哈哈哈哈,面对这种事你也有幽默感啊。”
“……平心而论,我很怕。”
“欸?”
“我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无所谓,但想到不能再见到的人和物,多少会有一点伤感。”
“……”
“嘛。最主要还是因为我怕痛啦,哈哈。”
“你刚刚把我拉进悲伤的氛围中欸!”
“毕竟这么悲观不太像是我的风格,或者至少说是不是我想要表现出来的风格。”
“……最后,还有一点事想要问你。”
“嗯?说吧。”
“你也知道我们两个的关系吧。”
“是绝对不会被祝福的那种呢。”
“对,其实我觉得把我们称呼为’我们‘都略显怪异。”
“所以,我不是很想打破现在的关系,不想失去身边的你。”
“但你也知道,一旦有我在身边,自己很有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停歇不前。”
“我毕竟是在为一个徒劳飘渺的目标努力着,身边的你是飘渺的具象化。”
“我也就成了你存在的意义。”
“最重要的意义。”
“这其实是在残害着你啊。”
“我不管。”
“……呐,你知道吗,人在掉落的时候重力加速度是9.8m/s²哦。”
“各个地区的重力加速度不一样吧,这只是个平均值……等等,你在干什么?停下!”
“不要走过来,再往前一步我就身子往前倾倒下去了。”
“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了,这样下去,遭殃的只有你一个人。”
“那你……”
“你再清楚不过了,我不过是你心里捏造的幻影,连你的第二人格都算不上,不管我在你心里的地位再怎么样,也终究是幻觉罢了。还是早点结束这一切吧,我这样子做的话,其实事后对你就无所谓了。”
“可我相信这幻觉。”
“……”
“说什么无所谓,你的死不是你一个人的,而是所有与你有关联的人,还有连同着我对你的所有回忆,所有我在你身上倾注的感情….所有的所有,也将与你而逝去。”
“……可是,如果我就此离去,这些东西也就与我并无关联了,何乐而不为呢?况且这是为了你好,其实。”
“与其让你在我的意识里离去,我更愿意承受灾祸。”
“……真是,感性到无可救药的混蛋呢。”
“我相信‘你’还有你是不会这样做的……我需要你。”
“……那么,请多指教。”